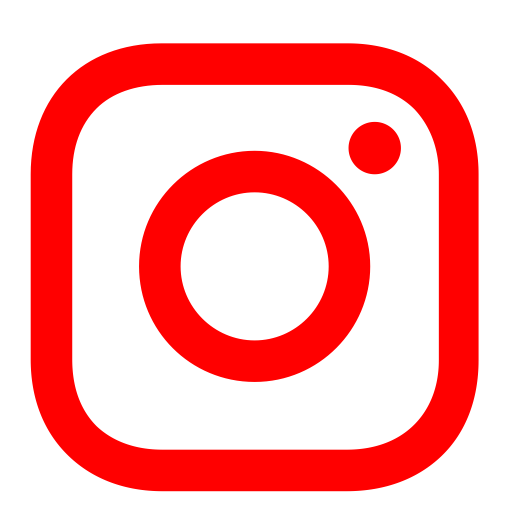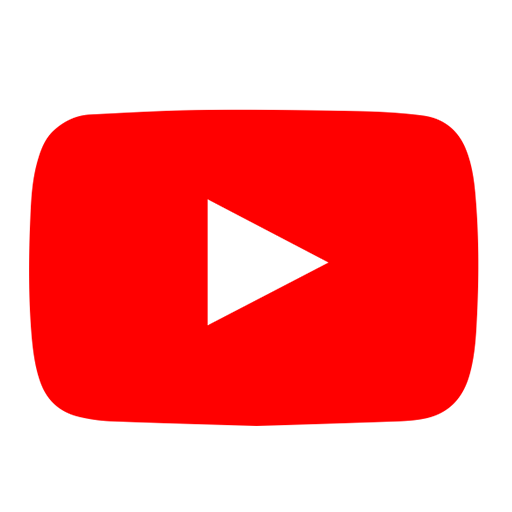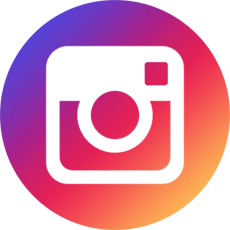思想家、文學評論家,70歲│台北市,2014年11月12日採訪
Text by 張世文 Image:courtesy of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
聊起自己,柄谷行人開場白就提到他上一次來台灣的經驗。他說,走在路上到處看到「小心行人」的標誌,「我的名字到處都是,好像在台灣我真的是一個名人。」他真的很有名,兩次來台,包括臉書、座談會不時冒出柄谷行人的名號,每次演講會也都有數百人搶著進入聆聽「大師教誨」,台灣彷彿在這兩年捲進一股日本左翼思想大師的熱潮之中。的確,台灣太需要一個有別於歐美的亞洲參照,尤其在近期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亞洲,柄谷行人的角色的確有其重要性。
從背景來看,他是個有趣的思想家──出身日本學運世代,1960年代曾參加反安保運動,也曾在1969年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獎,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在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他的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討論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他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更曾在2000年組織New Association Movement(NAM)運動,鼓勵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生產消費,對抗大財團資本。
從行動者、文學評論家到思想家,這樣的經歷看來多姿多采,但柄谷行人卻認為這並非是有「意識」的變化,「就像蘇格拉底受到Daemon(精靈)的指令,不以『公人』的身分進行活動,我的生涯經歷也是環境影響而發生。」1969年,他發表〈漱石論〉獲獎進入文學批評領域,2000年放棄文學批評試圖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柄谷行人認為這也是因為自然哲學──他定義中的「普遍宗教」──影響而產生的。
從行動內化的思想哲學
對於自己不斷變化的身份,柄谷行人笑說這是一種自我放逐,「這是一種因為想要逃避挫折而產生的心態。」從政治的挫折與不可為而轉向文學,其實並非新奇的事;從行動者轉化建構思想,這就是歷史的軌跡,「歐洲現代思想的建構,其實就是政治挫折的表現;由於現實上做不到,所以就轉移到觀念的世界進行革命。」柄谷行人說,不管是行動者或是思想家,其實都在追求一個自己所謂的理想社會,但這理想社會的形成,與參加者的「意圖」無關,而是自然而然、因為環境需要而產生,「簡單來說,一個完全自由而平等的社會,可能就是這些行動者與思想家所追求的目標;只是行動者希望改變世界,而思想家們改變的,則是對世界的解釋。」既然無法超越政治,就只好從思辨式的想像力中超越,轉化行動者的力量為文學的方式或許充滿無力感,但對柄谷行人來說卻是不得不的做法。
從自己的生涯脈絡出發,做為一個資深「行動者」,柄谷行人形容日本社會運動的看法相當有趣,「日本的民主化不是因為自己想要民主,而是一種對於過去歷史的反彈。」因為戰敗的關係,日本人厭倦戰爭,也因此透過民主化來否定過去的日本,這其實也有一點逃避的意味存在。日本人的心態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有些古怪,但柄谷行人認為,這其實也與國家在議題上的操作有關,「如果我們只以國家為中心來思考,是沒有辦法解決社會問題的,因此必須超越國家觀點,你才有辦法追求真正的平等。」
行動者思想家
這也是他在2000年決定捨棄文學批評家的身分,從新走回運動路線,「試圖以言論批評方式抵抗『政府即國家』的新自由主義觀點,終究是無力而行不通的,只有打破國家的視角,才有可能走出新的價值。」他說,以現在的民主制度來說,人民只有選舉那一天是「主權者」,之後只能服從他們的代表者──議會政治,而國家並非完全因社會需要而衍生出來,「國家不會順從社會的共識行事,也不會因社會共識希望它消滅而不見。」因此,只要國家存在,歷史仍會持續反覆,只有超越國家,才能重新思考。
雖然人們會把代表國家的議會,與示威、集會等對抗政府控制看作完全不同的東西,柄谷行人說,在某一瞬間它們會互相交叉,「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國家沒有辦法阻止做為主權者的人民出現,做為主權者的人民,一定會出來。」身為行動者思想家,柄谷行人對「人」的價值,仍然充滿期待。
柄谷行人
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判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及哲學等多元領域,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康乃爾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係、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他在1960年代參與反安保運動,日本311地震後,他發表《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獲得廣大迴響,也親自參與街頭反核遊行。;重要著作有《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哲學的起源》等書,是少數身兼行動者與思想家的哲學理論大師。
【完整內容請見2014年12月號君子時代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