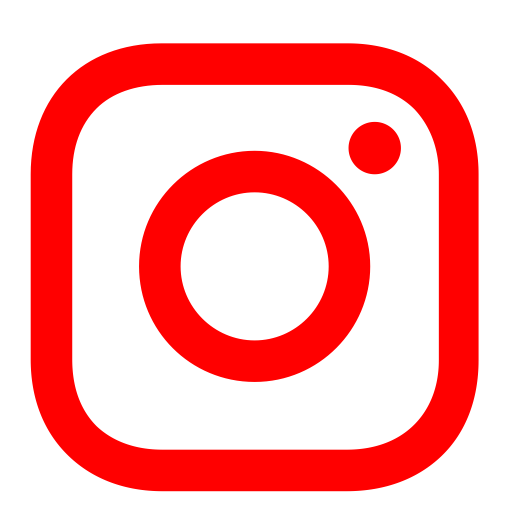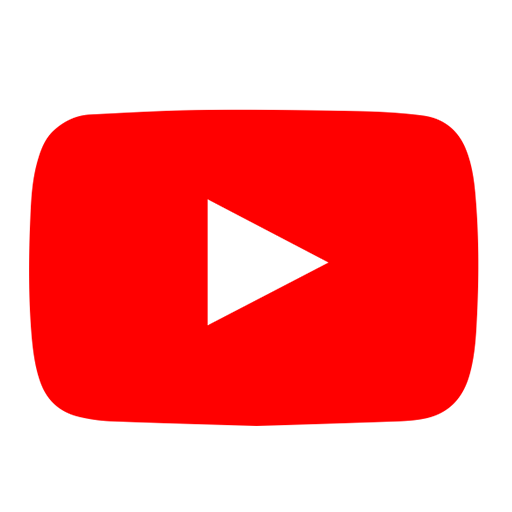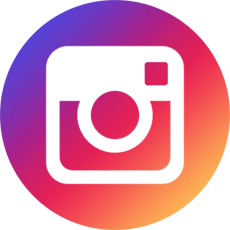《破風》是林超賢的新電影,這個名字取自於自行車團隊競賽的專有名詞──「破風者」,這個領騎者的另一代名詞,也似乎總是帶領團隊嘗試突破的林超賢很像。這一段專訪,是在前往記者會現場的保母車上進行的,Esquire趁著他滿滿行程的空檔,進行了一段訪問,談談他對電影的看法。
Text by 張世文 Photographs by林鼎皓 Images:courtesy of 華映娛樂、台北電影節
ESQ:謝謝導演!在你這麼繁忙的時候還接受我們訪問。
林超賢(以下簡稱L):沒有關係,其實就是閒聊,你不要問我太難的問題就好了!(笑)
ESQ:我盡力!不過這第一個問題好像就有一點複雜了。我想問的是,你從過去拍警匪動作片到現在拍運動電影,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L:其實,怎麼說呢?我覺得「動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節奏、一種速度,所以警匪片也是動作片,運動電影對我來說也是動作片。我以前也一直在想,有什麼可以類型的電影,可以把我在警匪片上學到的經驗,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重新表達,這個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ESQ:現在拍警匪片不是仍然很熱門嗎?為什麼會想要選擇不同的題材?
L:我總覺得我是跟時代脫節的電影人(笑)。怎麼說呢?我拍《證人》時,剛巧是香港幾乎不拍警匪片的時候,因為為了遷就大陸的市場,警匪片比較難通過電影檢查,所以既然大家都不拍,那我拍警匪片自然可以玩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現在大家又回來拍警匪片了,所以我就想嘗試些新題材,想來想去,我覺得做運動還不錯,於是從《激戰》開始開始嘗試從運動的觀點出發的片子。當然也是《激戰》給我很大的信心,是觀眾跟「老闆」也信任這種題材,所以當然就繼續拍下去了。
ESQ:你怎麼選擇你的拍攝題材?
L:選擇題材,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新鮮感」。舉例來說,如果《激戰》拍的是那種很傳統的拳擊片,我覺得那就不會讓人有什麼新的感覺;而且,我希望拍攝的題材是我熟悉與喜歡,像《激戰》的主題──「綜合格鬥」就是我過去就很喜歡看的競賽,而這次的自行車,則是我從2000年起自己就在接觸的運動。
ESQ:可以說,你的題材選擇最優先的考量,是從自己有興趣的出發囉?
L:當然,這跟跟著現在的流行趨勢拍片完全不同。你拍些自己喜歡的東西的感受,與跟著其他人用同樣題材拍攝是不一樣的,因為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出現在觀景窗裡,那種興奮感是完全不同層次的。
ESQ:所以拍這幾部電影,最初的初衷可以說是「讓自己開心」囉?
L:沒錯沒錯!我喜歡拍與自己生命中有關的事,因為有連結,才會讓你開心。
ESQ:你覺得會吸引你的題材,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L:拍電影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人物」,透過劇中人物所經歷的事情、產生的反應,看電影的人等於一起分享了他的喜怒哀樂,讓「他」與「你」產生一種聯繫,這是我覺得一部電影中最重要的元素。所以拍《激戰》時談中年危機,說的也是像我這樣差不多年紀的人,因此在電影的狀態裡,我覺得有一種為自己這種年紀的人「打打氣」的意味存在,可以說這個意圖跟自己的關係比較強烈。
ESQ:那這一次拍《破風》呢?
L:拍《破風》,則是有另外一種不同於《激戰》的感受想要表達。相較於過去,現在的年輕人似乎比較「急」,很急著想要搶第一,但眼裡面只有那個「冠軍」的時候,反而會看不到「第一」之外的其他意義。
對我來說,選擇自行車競技作為電影題材,是因為它的團隊運作方式跟別種運動不太一樣。自行車賽事是團隊的比賽,他們以六人或九人為一組參與競賽,我們看比賽時「衝線」時往往只有一個人,然後衝完線以後站在台上,所有人都覺得他是最好的,但還有更多的其他團員站在台下。
我一直覺得願意站在下面的人,雖然在表面上沒有獲得那些掌聲,卻能滿足於自己付出努力所得到的成就感,我覺得他們的心理素質真的很厲害。所以這次拍《破風》,有一種想要跟年輕人講一句:能為別人犧牲,來跟著團隊一起做一件事情,這是很可貴的情操。 
ESQ:這是否可以說是透過自行車運動,來談香港需要的精神呢?
L:嚴謹的說,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聯繫,我想講的可能範圍更大。其實我想說的,是每個人雖然都會有負面情緒,如果可以對抗乃至於衝破它,往後的世界或許會更好。當然我覺得現在是有種負能量在我們身邊蔓延,所以來做些有正能量的事,也可說是讓大家宣洩的途徑。好像《激戰》也有點這樣的味道在,它是希望透過正面勵志故事,讓看電影的大家能鬆一口氣、緩解緊繃的情緒後,再為自己的路尋找出口,是有同樣的想法。
ESQ:你覺得大家都太過緊繃了嗎?
L:過去香港確實在大環境下佔了先機,它有它地理上的條件,也確實有一種你剛剛所說的「香港精神」──人們願意刻苦、用最傳統的方法慢慢努力──讓它有機會從七○年代開始可以很快地在十幾二十年衝到一個高度;這個是一個美好的時代,但我覺得現在的人,已經忘了過去為什麼我們會願意去面對必須吃苦的環境,並從中找出生存的道理的力量,卻常常覺得「為什麼沒人關照我」,然後怨氣四射。
ESQ:怨氣?
L:對,那是怨氣。 我覺得現在的怨氣,來自於對環境的不滿。世界當然是不斷向前邁步,不會一直停留在好光景,也不會永遠都給你最好的條件讓你成功,所以以前我們說像街邊賣小吃的都可以變成大富翁的世界,可以說早就不存在了,當然就不應該再用「別人應該關照我」的心態,而是要開始學習去面對你在這個世界的逆境,並且想辦法衝破它。
逆境會在你人生中不停出現,不是電影裡那種你只要過了一關之後光明在望,不會的!所以,學習如何不被這種狀態打敗──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我覺得這是現在的人應該要有的精神,因為現在環境沒有過去那麼好了。
ESQ:那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L: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於自己的內心。因為,你必須自己去面對內心最大的敵人,只有內心裡的敵人才會真正打敗你,運動員經常會碰到這些事情,所以我拍這些電影,其實也有一點想告訴大家,甚麼樣的態度才是運動員的精神,百折不撓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在電影圈待了很久,我也經歷過自己在心態上的低潮,所以我從來就一種態度,就是今天做完一件事情,如果你滿意了,好,趕緊把它拋開,然後做下一件事──重新去面對下一件事情帶給你的挑戰,不管是困難啊!跌倒啊!還是一樣重複繼續做下去,你才會有一種更不怕面對難題的精神與條件。
ESQ:所以等於是說,你每次在拍一部新的作品時,都是把他當成新的開始去面對的囉?
L:對,而且每次都是要找一些新的難題給自己(所以,難度愈來愈高啦!)
ESQ:那像這次拍《破風》,你覺得最大的難題在哪裡?
L:(笑)通通都是難題!這一次拿自行車作為題材,真的需要體能才能應付,不只是演員,整個團隊的體能必須都一併提高,而且在拍片的時間都要維持巔峰,所以不管是演員或車手乃至於工作人員,都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力量,而且不是只有一天,是一段很漫長的時間。所以,這一部電影可說是這麼多年以來,最難搞的一部(苦笑,搖頭)。
ESQ:難在哪裡?
L:很多方面。從籌備到拍攝,到現在後製都有不少難題。 拍攝當下有太多不可預期的狀況,幾乎把自己逼到一度想放棄,畢竟拍攝單車電影,最難就是要掌握速度畫面,有時一個鏡頭要來回拍好多次,每位演員至少一天得騎超過五十公里,體能耗盡又容易摔倒,這一摔也會造成一群人受傷;這應該是我拍片二十年來最多人受傷的一部,很心痛啊!所以如果要我再選擇這類型的電影,我會多考慮一下了。
像現在做後期處理,就因為之前拍的素材很多、量很大,現在我必須跟好幾個剪接一起處理幕後;拍攝時放了很多攝影機去抓實境的不同角度,現在開始剪接才發現我幹嘛要搞得這麼複雜(笑)?不過,真的要這麼說,我也不懂我為什麼要去搞這麼多困難的事情,或許是我的命就是這樣吧!(苦笑)我也不知道耶!
ESQ:不過,你從過去《證人》到現在的《破風》,拍攝的調性似乎是愈來愈正面耶?這跟你的心態變化有關嗎?
L:其實從《證人》開始,我就希望能在作品中帶給大家「邁向光明」的感受,雖然每一部戲裡面都帶有黑暗觀點,戲裡主人公也常面對很多黑暗與壓抑的事,這也是反映我剛才說的「人生並不簡單」;但是在不簡單裡,這些主人公還是想要讓自己走出黑暗、邁向光明。
這可能不是每個觀眾都會看到的,但這都是主人公自己的「關卡」,雖然最後付出的代價很大,但是還是換到了他自己想要的。這是從《證人》到《線人》中,我想說的故事。但是在《激戰》我想詮釋的,則是比較要讓大家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意念,就沒有這麼隱晦了,但還是有同樣的主軸,就是希望人們能擺脫黑暗,走向光明。
ESQ:所以,透過電影故事,你會想要講嚴肅的道理嗎?這是你拍電影的目的?
L:並不都是嚴肅的道理。電影,其實在某個層面上,就是自己的一種紀錄。我在《證人》的階段構思時,其實我自己知道自己很痛苦,常常有很緊繃的感覺,所以我也需要用一些手段把自己的「臉」表達出來,讓自己得以釋放:有時候把自己放進黑暗裡面,從黑暗中又想看到光明,這大概是我當時的心情寫照吧!
要跨過低潮必須付出沉重代價,拍戲如是,生活也如是。過程雖然沉重但並不痛苦,因為主人公最終能換到生命中重要的東西,如此又哪怕痛苦?所以《線人》或是《激戰》中的困獸鬥場面都是為主人公設計的難關,要達到出口,就必須有付出的自覺。
像剛才說,比如我剛拍完一部電影,得到了算是不錯的成績,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候,我就會想:那我下一個應該要怎麼樣?下一次我要給大家什麼樣的新東西?這樣的問題,對我自己才有意義。 
ESQ:這是你想要滿足自己的成就感吧!
L:這個可能是一種滿足,讓觀眾下一次在看的時候會說:想不到林超賢又有不一樣的東西!這應該就是我的「虛榮心」吧!
就像說我拍《魔警》時,很多人都說:沒想到林超賢拍完很陽光的《激戰》,竟然會又跳到這麼黑暗的議題裡面!現在又跳脫出來拍《破風》,這起碼算是對我人生中的不同起伏的一種滿足感吧!這還滿有趣的。
ESQ:岔題一下,這一次拍《破風》,您跟很多台灣的電影人有不少合作,可否聊聊你與台灣電影人接觸的感覺吧!
L:我選擇跟台灣朋友合作,因為我想做一部「氣質」不一樣的電影,我不想讓人覺得還是做了個我已經習慣的創作。在香港拍電影,會容易讓人看到相同的舊習,不管是運作還是敘事都有。這種舊習已存在香港電影中幾十年了,雖然時代在不斷前進,但這些習慣還是一直存在;所以新的電影,我希望能做出不一樣的感覺,尤其因為這次在台灣拍攝的戲分超過六成,我很想在這部戲中放進「台灣的氣質」,做出與港片不一樣的感覺。
ESQ:什麼叫「不同的氣質」?
L:我覺得香港現在的工作人員,比起過去好像缺少些毅力,因為香港可以選擇的工作太多了,他們沒有那麼強烈的鬥志回來做電影這種比較辛苦的工作;但是我遇到台灣的工作人員,卻讓我非常驚訝與敬佩,包括助導跟機器組都是。我從台灣拍完部分的戲份後回到香港,還跟朋友說「我要帶這一組人回香港」,因為他們完全就是存在著我前面說現在香港人沒有的那種特質。 就像我前面說的,香港因為現在選擇的機會太多、太好了,所以那個基本的精神慢慢給現實磨掉了,但是我覺得現在台灣的工作人員還是有這樣的精神。
ESQ:拍了這麼久的電影,你怎麼看你跟自己的作品?
L:老實說,電影是個單打獨鬥的工作,拍電影很辛苦,我拍電影更辛苦,但不通過苦結果不一定理想,我覺得只有愈辛苦才能做得愈好。可能工作人員會覺得拍林超賢的電影太辛苦了,所以不太想理我,那好呀,你也可以找一些比較舒服的工作(笑),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我拍電影的精神。
2000年的時候我自己開始去騎車,我覺得騎車就很像我拍電影的歷程。騎車的精神不一樣,有的時候會上坡,上坡那種挑戰是最艱難的,如果你放棄的話,就根本沒有辦法再上去,你就停下來了,這有點像人生的起伏。有時候,我們騎車看到坡很陡會恐懼,然後問自己,我行不行?這個跟我們出來工作的那種心態很像,去跟別人去競爭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有這種狀況出現,跟人生一樣,很有意思,電影對我來說,也是如此。
【完整內容請見2015年5月號君子時代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