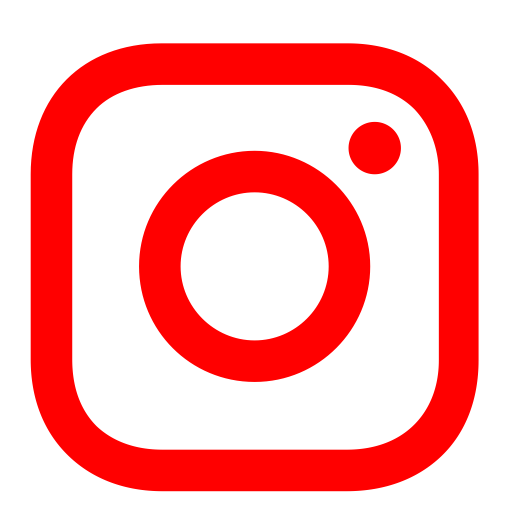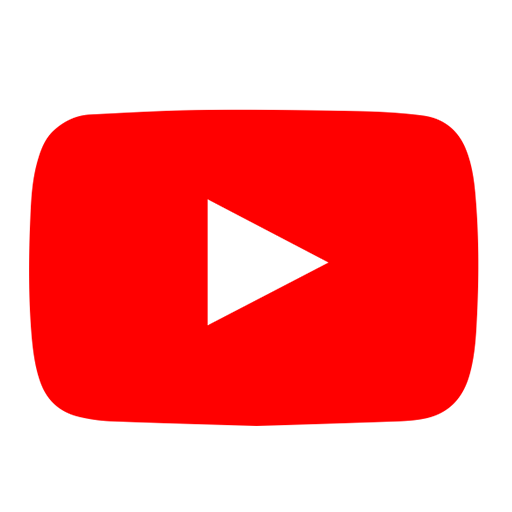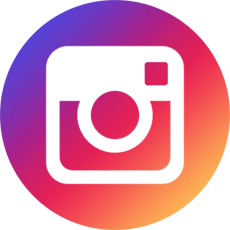攝影師、策展人、學者,55歲│台北市,2015年3月31日採訪。
Text by 張世文 Photographs by 林鼎皓
「當民意機關被占領,那些沒被分配到語言權利的人開始說話,議會原本的意義才顯露出來。」港千尋,這個身兼策展人、藝術家與學者於一身的一個人,在今年出了一本書,這本書談的不是當代藝術、經典展覽或是攝影作品,而是去年三月台灣的一場運動。這場佔領立法院的行為,在不同意識型態角度的人眼中,或許存在著不同的意義,但自八○年代以降,由於全球化加速,各國公民運動在這股浪潮下風起雲湧,一次次民主出路的新「實驗」中,這個關心公民運動、長期走訪各國運動現場的藝術家兼研究學者,卻在這場運動發現了不一樣的東西,「我稱之為──革命的做法。」 
發現他者
這場運動,算是一種革命?港千尋看出了我的疑問。「對我來說,暴動或暴力行為這樣的事情,確實在發生大規模革命的時候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對我來說,暴力行為並非在革命中會必然發生的事情。」他說,從法國大革命以降,暴力似乎永遠伴隨著革命而來,當然「奪取或置換權力」這件事,透過暴力當然比較簡單,但事實上如果要達到目的,是否可以非暴力的手段來達成,這其實是有可行性,而且應該要被優先思考的,「不過,對我來說非暴力並不是『不抵抗』,而我想闡述的其實是如何用『除了暴力之外的方式』來達成『抵抗』的效果,所以所謂的革命的做法,其實也可以說是人類如何用『創造力』達成自己的目標。」
「我對台灣的社會運動感到興趣,並非是從佔領立法院運動而起,而是樂生院的保存。」2009年,港千尋與藝術家岡部昌生前往樂生院,與當地的住民跟參與保存運動的青年學生們進行的拓繪工作坊,「我當初會跟岡部昌生前往樂生院的原因,是以『藝術家』的身分進入的。」當初港千尋跟岡部昌生選擇樂生院來進行拓繪的原因,主要因為它是日據時期的政策所留下來的建築,對台灣來說這該是一個被禁止與否定的區域,「但很奇怪的是,這麼老的一個東西,卻有一群台灣的年輕人希望去保存它,這是讓我覺得很有『共感』的一件事。」樂生院遇到的年輕人讓港千尋覺得,台灣似乎非常重視對於歷史與記憶的保存,也很重視這些歷史記憶。
當然,以日本人身分到場的港千尋一開始其實有些尷尬與糾結,但與這些已經在院裡待很久的院民一起進行工作坊與對話,卻讓他感到震撼,「這些院民們最後還唱了一首日文歌送我,讓我在情緒上控制不住、有些感動。」他笑說,在台灣他一直提到的care(關懷),最初就是在樂生院感受到的,「因為我覺得我一個外人被應該是我去關懷的人關懷了。」他說說,care這件事要怎麼一言以蔽之,其實就是「發現他者」,「當你願意進入對方的處境觀察,你才有機會了解事件的全貌。」港千尋說,這其實是他談「革命的做法」的初衷。
社會運動的創造性 港千尋說,巴西在2001年的憲法中列入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的概念──都市空間的使用價值,永遠必須優先於它的交換價值──我們今天都市的街道、房舍、建築常以商品化的觀點來看待,所以如果公民對於這個社會有不同的構想,在目前的狀況下的確沒有發聲空間,因此巴西在把都市權列入憲章的思維,影響了後來美國與德國都市權運動的發展,甚至這樣的觀點進入近期,包括佔領華爾街甚或是茉莉花革命都存在著相同的脈絡。於是,從都市權觀點置入世界史的社會運動系譜裡面來看,佔領立法院的確並非是單純的政治運動,「就社會運動的角度觀察,群眾佔領民意機關以及附近的街道,就是以『佔領』的角度呈現的政治權要求。」港千尋認為這可說是「都市權的重新伸張」,也與群眾語言、身體、感性與知覺的形成有關。
這的確是具有攝影美學的思考角度。以宏觀角度,可以把佔領立法院運動放入歷史譜系找出一以貫之的脈絡,但以微觀角度來看,這場運動也呈現出更多意義。就像羅蘭巴特曾經說過:攝影本身就是一個多異性的、絕對不會是意識形態的呈現,影像本身的確可以有不同的解釋面向,包括編排方式、它所形成的蒙太奇等,都是對運動的有趣拆解,「他們怎麼去構造這個我所謂的革命,是一件一件具體小零件的設置而形成。」透過眼睛與觀景窗觀察、遊走與接觸,的確構成了一個當代藝術家眼中的「作法」,這也是港千尋眼中社會運動的「藝術」焦點。
【完整內容請見2015年7月號君子時代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