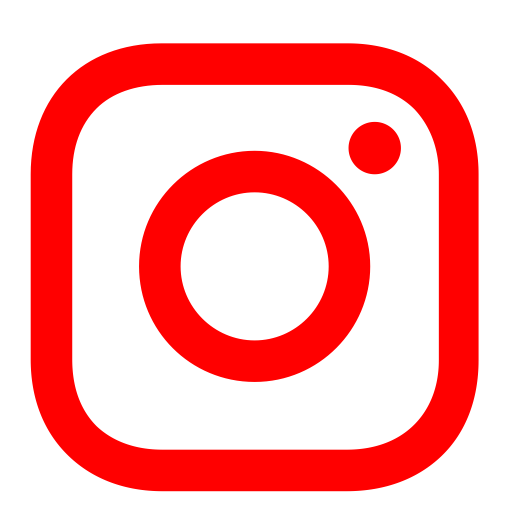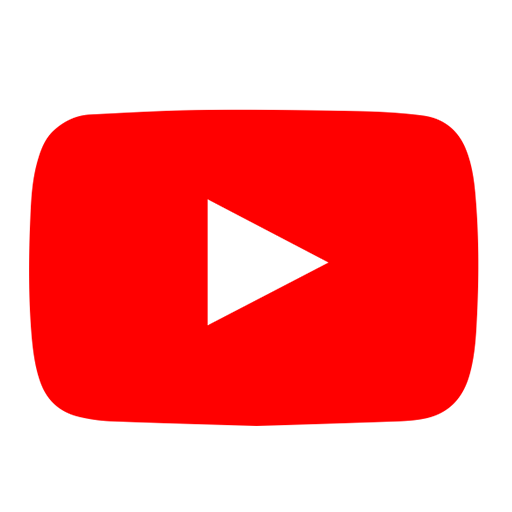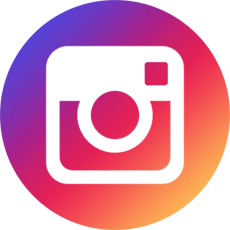出身內蒙古、年僅35歲的中國導演張大磊,若干年前還是個玩搖滾的慘綠少年,誤打誤撞跑去俄羅斯學電影後,憑藉著靠拍婚攝所掙的錢,他拍出了人生中第一部長片《八月》,這部簡單的抒情小事觸動了金馬評審,獲得第53屆金馬獎最佳影片殊榮。日前電影在台上映期間張導本人親自來到台灣參與各大映後座談,《Esquire》與他約在一個暴雨午后,聽聽他怎麼看待自己的作品,和閒聊,不敢說投緣,但起碼我們都是Kurt Cobain的信徒。
Text by 郭璈 Photographs by Wu Chin Tsan 化妝&髮型 by Angela Chiang Images:courtesy of 前景娛樂 Special thanks To 光點紅氣球
所以,我們從Nirvana開始。
和大部分Kurt粉不同的是,張大磊最喜歡的Nirvana專輯是1989年的《Bleach》──這張只花40小時便錄製完成的debut,而不是那張石破天驚的《Nevermind》,「還有,還有一些B-side歌。」張大磊補充,他說話時的皺眉表情,彷彿每句話都再三確認後才說出口。《Bleach》象徵Nirvana尚未爆紅時的未染世俗,那種原始的狂躁與形狀正吻合大磊心中對搖滾樂的想像。青少年時他也與諸多地球上的搖滾少年們一樣,在某個煩躁的午后、因為音響裡的某首歌而有感於自己被拯救,胸中某種開關就此開啟,然後組了個自己的樂隊,從cover開始、接著創作,然後,遇上人生的分歧。
照他自己的說法──他當時離搖滾樂太近了,所以他放下了吉他與麥克風,選擇單純當個樂迷,這種「保持距離」的哲學也間接反映在他的電影裡,在《八月》裡,他透過小雷(孔維一)的孩童視角去觀察世界,孩子的純真始終與這個世界保持距離,然而觀眾視角也同樣保持一種空隙。這種帶有距離感的冷靜視角,可脈絡於侯孝賢導演啟發自《從文自傳》一書的拍攝思維。大磊的父親張建華本就是電影剪輯師,高中輟學後的大磊原本毅然決然跑去俄羅斯學音樂,但到了那邊才發現所謂的音樂本科都是走正統古典路線,臨門一腳改修習電影,繞了一大圈,還是接上與老爸一脈相承的電影人命運。
和諸多偉大的藝術工作者一樣,大磊第一部作品選擇回溯內心深處的私密記憶,他把兒時真實發生的情境擺在你面前,那是屬於夏季的白日夢與回憶,引領觀眾回到1994年中國內蒙古的呼和浩特,那年Kurt Cobain自殺離世,但大磊並未想做出任何具有少年憤慨的作品,對他來說,1994年最大的衝擊便是中國國有事業轉型,原本在國營製片廠擔任剪輯師的父親失去了鐵飯碗。建立在此背景下的電影劇情很簡單,主角小雷是個剛結束小學生身分的準初中生,在一個沒有暑假作業的悠然夏日裡,以他視角為主體,讓大家看看整個八月裡,究竟有什麼事被改變?或沒改變。
但我們都知道越是平凡的事其實是越難拍的,《八月》是部沒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的電影,但Esquire還是有很多問題想問問這位搖滾青年兼導演,一些關於電影、或無關電影的事。
(以下將提及《八月》部分劇情與內容)
ESQ:呼和浩特(中國內蒙古)是個什麼樣的城市?
大磊:挺無聊的(笑),大概就和每個人腦海裡的「家鄉」二字差不多吧!生活了幾十年、20年、30年都在那兒,青少年時我滿腦子想的就是離開那兒。
ESQ:拍像《八月》這樣一個以你生長背景為主體、一個屬於創作者內心私密的故事,會需要很小心去處理很多事嗎?會否有點近鄉情怯?
大磊:我是很小心地處理很多事,但真要考究起來,也不會是因為故鄉的關係,而是因為「人」,人與人的情感才是決定這座城市之所以變成家鄉的原因。
ESQ:電影一磨就是7年的時間,這7年間,是否讓作品有了意想不到的變化?之前聽聞本來片名不叫《八月》,而是《曇花》。
大磊:是的,曇花是電影裡頭一個重要的象徵,電影從籌備到開拍經過了好多年,可能因為等待久了,要說這7年間最重要的改變,就是我越來越能用一種「冰冷」的心情去看我的作品,一開始是抱著「一定得說些什麼」的心態,後來我就不這麼想了,也覺得用曇花命名會太藝術,想要簡單些,「八月」這名字就挺簡單的,讓人不要想那麼多。改片名是最後才決定的。 E
SQ:我們知道《八月》一開始就篤定要拍黑白電影,那連現場監看的monitor也是黑白的嗎? 大磊:沒有,現場監看螢幕是彩色的。
望著母親替曇花澆水的小雷,小演員孔維一這段發自內心的微笑其實是意料之外的NG,孔維一也憑此角獲得第53屆金馬獎最佳新演員。
ESQ:這樣在後製上會不會遇到落差?
大磊:有的,但即便我們打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拍黑白電影,但在拍攝過程中我們一直在尋找更多可能性,我們也很期待彩色畫面,說不準效果很好,所以並未依照黑白片的方式去佈置光影,所以你會看到最後電影畫面的黑白反差與對比其實沒有很大,最終呈現出的感覺是「有一點點色彩的黑白」。
ESQ:片尾最後一幕的安排,也是一開始想好的嗎?
大磊:那幕是補拍的,是剪輯到幾乎最後一刻才想出來的。我的想法是……要給父親這個角色的安排一個交代,不能說我們最後看到這位父親好像是妥協了、低下他高貴的頭顱(電影裡的梗)。我是覺得至少要讓大家知道他在做什麼?看看他在工作的樣子,他還是待在電影工業裡。
ESQ:談談導演與演員的關係,你是怎麼和你的演員們一同創作這個電影的?
大磊:和成年人的演員──爸爸媽媽(張晨、郭燕芸),我只和他們聊生活,聊他們自己在那個年代的生活樣貌,然後,聊我對那個年代的想法,大家彼此都熟悉,我會很清晰地介紹我劇本裡的每一個角色給他們認識──就好像介紹個老朋友一樣,有點像徵婚(笑):「這個人呢!他怎麼樣怎麼樣的、家世背景如何?興趣嗜好是什麼?」有個特別清晰的了解後,演員們就會帶入他們自己的生活經驗裡去平衡這個角色。和小雷(孔維一)嘛……畢竟是個孩子,我和他反而說得少,不會和他解釋太多。
全片啟用的都是素人演員,包含最重要的小雷一家三口。
ESQ:但他(孔維一)表現很好,令人驚艷,在現場會有什麼失控的地方嗎?
大磊:有(笑),很多,小孩就是這樣,他不懂大人們的感受,累了,會哭,不想拍的話,誰去勸都沒用。就慢慢來吧!我就像個壞叔叔,去拐他、誘他,讓他一步一步完成我想要的畫面。
ESQ:《八月》都是素人演員,你如何去挑選你想要的演員?
大磊:基本上我還是按照劇本去挑的,挑那些本來就和角色相像的人,張晨、郭燕芸、和孔維一,他們本身就帶有劇中人物的特徵和氣質。
ESQ:小雷這個角色可說是導演你個人兒時的投射,飾演者孔維一有特別像小時候的你嗎?
大磊:有一些,有一些,像是安靜的時候,我們都是挺靜的孩子,或是那種,莫名其妙的,不知在想什麼?就像有場戲,運動會之後,他從操場走出來,所有人都走了,就小雷一個人站著,也不知要去哪?望著和大家不同的方向,那種感覺特別像我。
導演透過電影裡小雷的孩童視角去重現他腦海中屬於那個年代的白日夢。
ESQ:你會怎麼去觀察、評論一個演員?
大磊:倒不是說什麼好壞,我覺得還是看每場戲裡的表現吧!我的理解是「不要輕易讓人看出演員在做什麼」,沒什麼大動作、大情緒,卻能讓我們感受到他在想些什麼,我覺得這就是好演員。
ESQ:小雷夢境裡,夢到三哥在河邊殺羊的那一幕,對你來說具有什麼樣的意義或象徵。
大磊:那真的是我兒時的一個夢,是我從小學到中學經常夢見的一個場景。我雖然生長在內蒙古,但我父親老家在河北,我沒去過那兒。我覺得那是一個孩子對籍貫故鄉、對不了解的事物所抱持的想像,我其實並未想要透過這幕去隱喻什麼,但我後來看到網路上有人幫我分析、解夢,他們說宰殺牲畜的夢境,暗示著父母的工作遭遇變動、可能即將遠行等等,對照電影結局與當年的我來說其實也挺對的、挺玄的。
ESQ:電影海報上的宣傳詞是「留住好時光」,對你來說,說私心也好、刻意也罷,你最想留住的是哪一個部分?
大磊:這句話不是我想的(笑),要說留住嘛……我並沒有想要透過《八月》去傳達什麼大道理、也沒有想要緬懷、懷舊任何時代感,我也不想它有什麼作用。
ESQ:它其實比較像是一種抒情。
大磊:對,純粹的抒情,這部片就像我的一個白日夢,我挺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我也不會說什麼九○年代比較好、過去比較好、現在就不好等等貴古賤今的話,也許今天挺好的、明天就不好了(笑),這種事誰知道呢?
小雷與擔任電影剪輯師的父親一同看膠卷,這幕是張導特別對義大利名導朱賽貝托納多雷(Giuseppe Tornatore)的《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的致敬。
ESQ:電影末段,小雷放下了他整個八月帶著不放的雙節棍,象徵著他的蛻變,《Esquire》其實滿強調這種男孩與男人之間的關聯性。現實生活中,那怕只有一秒也好,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你自己「放下雙節棍」的心情或場合?
大磊:經常會有,拿起又放下的,太多了這種場合了,我覺得你說的那種關聯性挺好,我自己更相信──男孩是心理上的、而男人是不可抗拒上的生理與時間變化,你終究是要長大的,但長大也並不是一件好事,保持像個男孩這是心態的,對我來說特別珍貴。好像電影裡頭小雷的父親,我覺得他就是大男孩,有一幕,他獨自在客廳裡笨拙地打拳、然後扯掉那些錄影帶,他在給自己壯膽,壯膽去成為一個男人,但其實那不是成長、而是看清。
ESQ:怎麼分辨每個當下是男孩或是男人的狀態?
大磊:如果是男孩,看見一個蘋果,他就會跟他媽說:「媽,我要吃。」但如果是男人,就算心裡想吃、特想吃,他依舊要拿起來放到身旁的女孩面前,說:「你想吃嗎?這給你。」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ESQ:拍完《八月》後,到下一個作品的創作階段,對你來說是令人興奮的?抑或痛苦?
大磊:下一部作品的劇本其實很早就在策劃了,甚至還早於《八月》,所以現在算是都還在計畫之內,覺得挺好的。下一部片的背景是設定在一個中俄邊境的小鎮,畢竟我在俄羅斯念書,對那兒比較熟悉。
ESQ:如何在「電影創作者」和「電影愛好者」兩者間取得平衡?
大磊:這個我到現在都沒做好。前天我才和廖桑(廖慶松,台灣新電影世代最重要的剪輯師)聊到,我受侯導(侯孝賢)作品影響很深,所以我也很清楚地明白,侯導電影的氣味是非常適合我的,但同時間我也很迷戀蔡明亮導演的作品,可他們兩人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在拍電影時自然而然會下意識地遊走在他們兩人之間,我的創作很容易隨著我各個時期的觀影喜好而有些微的變化,這往往會耽誤我很長一段時間,最終我還是得設法回到屬於我自己的位置,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斷地試,試到找出最適合我的東西。
ESQ:當然張導你也還是很年輕,但如果要以過來人的身分給予對電影工業同樣有夢想的年輕朋友們一些建議,你會對他們說些什麼?
大磊:單憑我僅有的那麼一點點經驗,我想分享給年輕朋友們的是……少想,別想太多,當然關於前期創作的部分可以多想點,但對於「如何完成」這件事,少想點,因為現在很容易就可以去拍片了,不是那麼複雜的,就先拍吧!智慧型手機也行,拿了就去拍吧!別想太多,就是去做就對了。
ESQ:大概什麼時候你自己領悟到這種「別想太多」的哲學?
大磊:我一直都是,從接觸電影、開始拍電影以來就是這樣,我其實沒有把電影這件事看得太重,我覺得把一件事兒看得太重就不好了,想到了,就去實現一下吧!這樣比較自在,大不了就失敗吧(笑)!我總這麼想。
八月》是張大磊獻給父輩們的抒情。
ESQ:你覺得父親影響你最深的部分是什麼?
大磊:我爸從小就耳提面命地對我說:「性格決定命運。」我還沒上小學他就跟我說這番話,我在年紀很小時就常常在思索這句話,想不明白(笑),還太小了,但至少會去意識到這件事──性格決定命運。有時候生活遭遇了一些困難或波折,我就會自問自答這句話,「我是個什麼性格的人呢?我應該怎麼做?」想明白了後很多事情就能解決了。
ESQ:你會怎麼形容你自己的性格?
大磊:嗯……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不是那種太張揚的人,但我知道自己在堅持什麼,我很任性,我還滿確認這一點的,所以每次捫心自問確定自己是這樣子的人後,做很多決定就不會猶豫了。
ESQ:家人以外,影響你最深的人物是誰?
大磊:Nirvana的Kurt Cobain,不光是音樂層面,也影響了我的處世態度。
ESQ:Kurt的死對你來說有什麼影響或啟示?
大磊:我開始聽Nirvana時他已離世了。我覺得Kurt的死是源自於他那敏感的性格,一方面他希望他能夠完美得到認可,但另一方面又厭惡名利,一部分的他乖張暴戾、而另一部分又是憂鬱低迷,他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他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就像我前面說的:性格決定了命運。他的自殺是注定。
ESQ:後來沒有繼續經營你的搖滾樂團的原因為何?
大磊:那時候覺得,我離搖滾樂太近了,真要放下一切讓自己變成一個搖滾歌手這件事我感到有點不舒服,我發現我喜歡音樂、而不是當個音樂人。
ESQ:但你現在還是有在創作音樂,例如〈有雲的日子〉,還會有想要弄些什麼的衝動嗎?
大磊:有的,我覺得現在這樣比較輕鬆,如果關於電影的事情比較不忙時,我還是會和幾個朋友去弄些音樂的東西,沒什麼壓力,而且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我就是沒法將一切置身事外然後專心做個音樂人,我沒辦法,所以現階段這樣是個挺好的狀態。 
*電影《八月》現正上映中。
完整內容詳見Esquire國際中文版2017年第143期7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