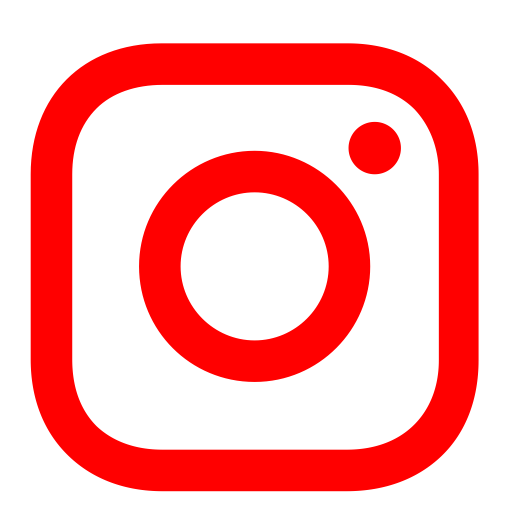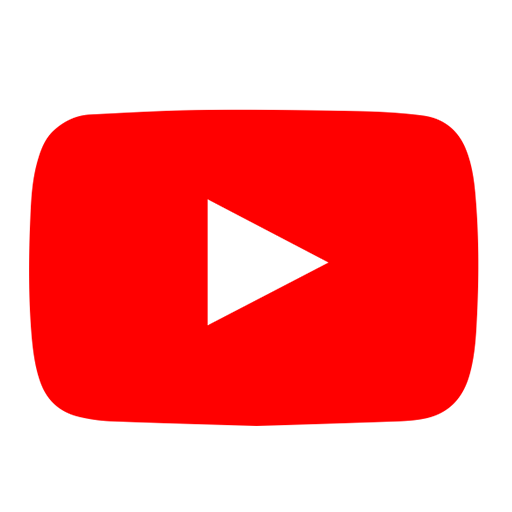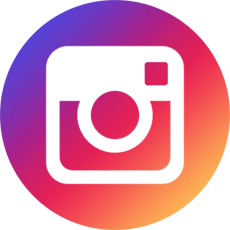「人活著,是不會好的,會一直痛苦,一直痛苦。從出生的時候開始,就一直痛苦,以為換了個地方會好,好個屁......只會在新的地方痛苦。沒人明白它是怎麼存在的。」
 《大象席地而坐》電影導演胡波
《大象席地而坐》電影導演胡波
《大象席地而坐》在2018年風光拿下金馬獎最佳劇情片,但編輯我卻居然拖到了2019年才有機會在戲院看見這隻「大象」的真面目(覺得羞愧。四個小時的片長對於任何觀眾都是個「挑戰」。編輯在看完電影後,對於許多觀眾認為本片的是一場「純粹的悲劇」這個想法相當不以為意;胡波作為一位有才華的導演,描繪出這一代(中國人)群體的生活,有悲劇,當然也有喜劇、有悲觀,自然也會有樂觀。
就像是法國名導楚浮的《四百擊》、義大利名導費里尼的《浪蕩兒》,或者是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侯孝賢更曾在訪問時,提到他深受此部片與導演胡波的感動:「坦白講非常感動,嚇了一跳,真的很厲害!比我們年輕時候拍片還更好!」)。

這些偉大的導演都曾經在年輕的時候,試著用鏡頭描繪那一代年輕人所面對的徬徨與無以名狀的憂鬱;但胡波在《大象席地而坐》中的野心更大,除了對於青春期男主角面臨愛情、友情、親情與自我認同的煩躁;他更用了其他不同年齡、性別的角色來隱喻這位「主角」,同時反映出這些在觀看電影的我們,在人生中所可能會面臨的困境與一切。其實這部片像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籠罩著一股鬱悶的高壓氣氛,這兩部片除了片長都很長之外,也都訴說了生活中那些被「不可說」的力量所操控而顯得無能為力的我們。

「其實很多事情我都不覺得什麼,我按流程來的,怎麼就成了這樣?」
電影中的人物不斷得在不同空間架構的「牢籠」中穿梭,而很多時候,導演不讓我們看見演員的「正面」,逼著觀眾就像是電影裡的角色一樣,在無助徬徨下「面對」這「一堆破爛」的生活。一如卡夫卡的小說《城堡》中的主人翁,在充滿著荒誕變形,且帶有敵意的環境所孤立;卡夫卡用這本小說描寫現代人面對龐大「制度」下的困境。一如《大象席地而坐》中的每一位主角,都被「宿命」般的不幸所籠罩;鬼魅般在街道上攻擊人與動物的「大白狗」、微信裡大大小小的「群」藉由好奇心的人們來傳遞散播有害的消息八卦,當然還有家庭、學校、警局、幫派等一層又一層「他人即地獄」的人情世故。

若是說導演沒有藉著電影來暗喻中國的政治狀況編輯我是不信的,又或許他只是被李安口中的「電影之神」所引導,不自覺地做出這樣反映社會現況的劇情、剪輯與電影。而作為一個創作者最勇敢的是,就是他完成作品的最後一刻,決定堅持自己在創作時被感招而「無意識」所做出的犀利觀點,而能夠不畏懼當權、審查壓力讓作品本身說話。比起許多曾在過去拍出「擲地有聲」作品的中國的導演,但現在卻淪為「人不人、鬼不鬼」樣貌的作品,胡波以初生之犢之姿做到了創作者最不該遺忘的「本心」。

所以「席地而坐的大象」到底是什麼?它可以有很多面向與解釋,或許是侯麥電影《綠光》(Le Rayon Vert)中不斷追尋愛情的女主,最後在結局時的日落看見的「綠光」(看見、聽見了大象);它也可以是宿命般受困於馬戲團牢籠無法逃脫的象;又或著是在生命荒野中,坐在「此地」努力著且一邊希冀未來的象。片中每一位主角對於這「席地而坐的大象」都有其不同象徵意義,也讓它豐富了電影的觀點、觸及了不同的觀眾。
男主就像是卡繆筆下的《異鄉人》,似乎不帶任何情感的面對生活的困境或問題;但我們在他這樣看似對生活「漠然」的態度之中,卻又由他對待好友自始自終的信任、對於失手殺害對象的懺悔看見了一絲人性的溫暖與光輝。

「你能去任何地方 ,可以去。到了就發現,沒什麼不一樣的,但都過了大半生了。」
而也是因為有男主角這樣帶點傻勁卻又無用「人設」,以至於在片尾當老人悲觀得(卻又樂觀認命得)認為,這個世界與存在的問題永遠不會改變時,男主卻幽幽得吐出一點眇眇的期待和希望。或許這也代表了在這殘破世界中,殘存在潘朵拉寶盒(Pandora's box)底下的「希望」。所以用另一個角度來說,《大象席地而坐》是一部再樂觀、再豁達不過的電影了,就算生命中的痛苦會一直存在,而也「沒人明白它是怎麼存在的」,我們還是像推動巨石的薛西弗斯(Le Mythe de Sisyphe)不斷地離開、尋找、抱持希望、又不斷失望。詩人韓波曾說:「在富於詩意的夢幻想像中,周遭的生活是多麼平庸而死寂,真正的生活總是在他方。」而那隻「大象」也從來不在我們腳下,而是在即將啟程的「他方」。
Text by FRED FENG Images:courtesy of 網路、繁盛映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