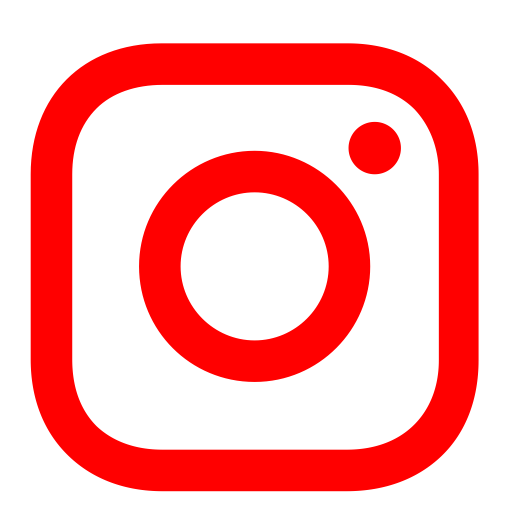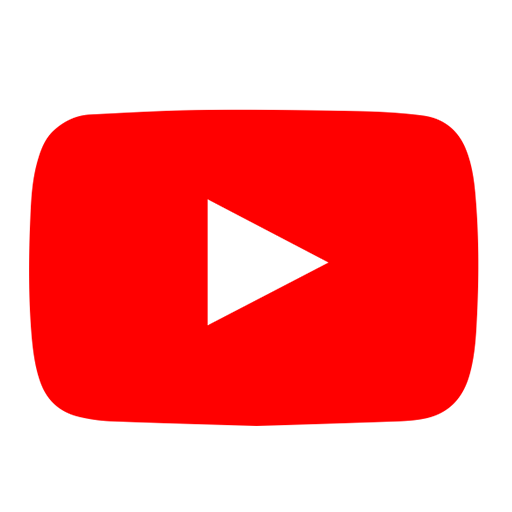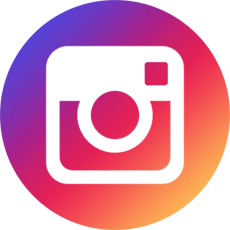看著莊東杰拿著量杯、滴管,用威士忌調製自己的作品,其實有些錯亂,好像眼前的指揮家似乎是個魔法師。這是Johnnie Walker的「調和實驗室」現場,穿著實驗服、手上沒有指揮棒的東杰似乎還有些靦腆,調製好的作品──原來叫「第五號交響曲」,實驗做到一半改名為「第三號交響曲」的調和式威士忌就放在手邊。問起「改名」的緣由,他笑了:「你知道嗎?剛剛站在那些『實驗器具』前面,我有種一個指揮家第一次站上指揮台的感覺,雖然他從來沒有指揮的經驗,但卻不只一次在腦海中演練指揮的感覺。」
莊東杰可以說是古典樂界的新星。2015年,他甫於2月在德國剛拿下蕭提指揮大賽亞軍,接著又於5月在丹麥拿下馬爾科國際青年指揮大賽冠軍,當年這一場來自全球各地317位青年指揮家共同參與的馬爾科國際青年指揮大賽,被音樂界視為「指揮家的奧運」:評審從參賽者中選出24位入圍者,到哥本哈根參加為期5天的4輪比賽,最後由進入決選的3位最終參賽者指揮丹麥國家交響樂團,演奏者指定樂曲。東杰指揮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第一樂章,及丹麥作曲家卡爾.尼爾森(Carl Nielsen)的歌劇《假面舞會》選粹,深獲評審青睞,認為東杰詮釋布拉姆斯曲目「掌握曲意卻又新穎」、「音色細膩度極佳」,因而奪冠。
提到樂團指揮,大家恐怕第一個到的就是《交響情人夢》裡的情節,這或許也是台灣一般人對於指揮最基本的聯想。問起東杰站在指揮台上的感覺,他說得有些玄妙:「有點像是人生混搭的感覺。」他說,當你要指揮一個作曲家的作品時,有點像是指揮者與作曲者在人生經歷中所擦出的火花,舉例來說,可能現在要指揮貝多芬的作品,你一定會想要去接近當初貝多芬創作這曲子時的原有意象,但我不是貝多芬,我也不可能有貝多芬如此的人生經歷,於是乎在指揮作品時就會有些卡卡的,「所以如果要指揮好一個作品,你一定要想辦法變成那個人,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情境中,你還要感到free。」他說,當你轉化成那個人時你不會感到恐懼或疑惑,在其中仍能自在悠遊,就是指揮的最高境界,「這其中最大的關鍵字,就是那個『感到free』。」東杰說,其中的關鍵在於自己必須非常了解自己,才能自然地說出自己的人生故事,「你扮演貝多芬可能有些奇怪,因為貝多芬已經死了這麼久了,你根本不可能實際地認識他;當然,你扮演你自己也很奇怪,因為自己無法詮釋自己的生命故事,交給別人來闡述其實比較客觀。」在客觀與主觀間迴盪,似乎就是做一個指揮家在詮釋作品時的最大挑戰,「這也是有趣的地方,讓我長時間樂在其中的原因。」
生長在音樂家庭的他,其實也有一段不想與音樂為伍的日子,「你能想像我高一以前班上幾乎沒有男生的狀況嗎?」東杰說,在高一時他突然發現,過去人生所接觸的人事物似乎都太過雷同,「我更害怕我的未來也是一樣的狀況。」當你不斷看到同樣的人,你可能會把自己塑造成跟你一直接觸的人愈來愈相像,「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要離開這個圈圈一趟。」大學回到「一般生活」念統計,東杰覺得雖然這只是給自己離開音樂的一個藉口,但卻是他重新豁然開朗的一個經驗,「我常比喻你的世界如果有一個核心,這個核心中有很多待解決的問題,但把視野拉大,你會發現在這個核心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球體,它有無限的角度可以切入這個核心。」他發現做音樂不是為了音符,做音樂不是為了演好一首曲子,「而是做為一個充分瞭解自己的途徑,讓自己再下一次演出時更能站到那個『平衡點』的過程。」當一切豁然開朗,整個世界觀都完全不一樣了,「我很慶幸我自己走了這樣一遭,讓自己發現音樂還是最愛,但不一定要用鑽牛角尖的態度去看待這件事。」
東杰說,他很喜歡柏林愛樂總監賽門拉圖對指揮的詮釋──指揮是我所知唯一一個「隨著年齡增長而愈發困難」的職業,而這也是他願意重新走回他「音樂道路」的動力,「當初我本來只是把指揮當成回到音樂圈的手段而已,當進入了指揮的領域才真正發現其美妙之處。」隨著人生的歷練,對於樂曲的解讀當然會愈發洗鍊,而透過這樣的反省也會讓自己的生活產生更多的哲思,問他為什麼讓音樂成為自己的夢想與人生目標,他想了想:「或許就是因為每次接觸它都會讓你有不同的成長,才讓我有前進下去的新動力。」東杰說,「無入而不自得」是他追求的人生目標,「而音樂,就是讓我能前進去尋找這個境界的鑰匙。」
同場加映: ﹝夢想進行式﹞ 跑步哲學家 陳彥博 帶出台灣的美 季裕棠 台灣第一支全裝美式足球隊 台北獵人隊 攜古宴今 張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