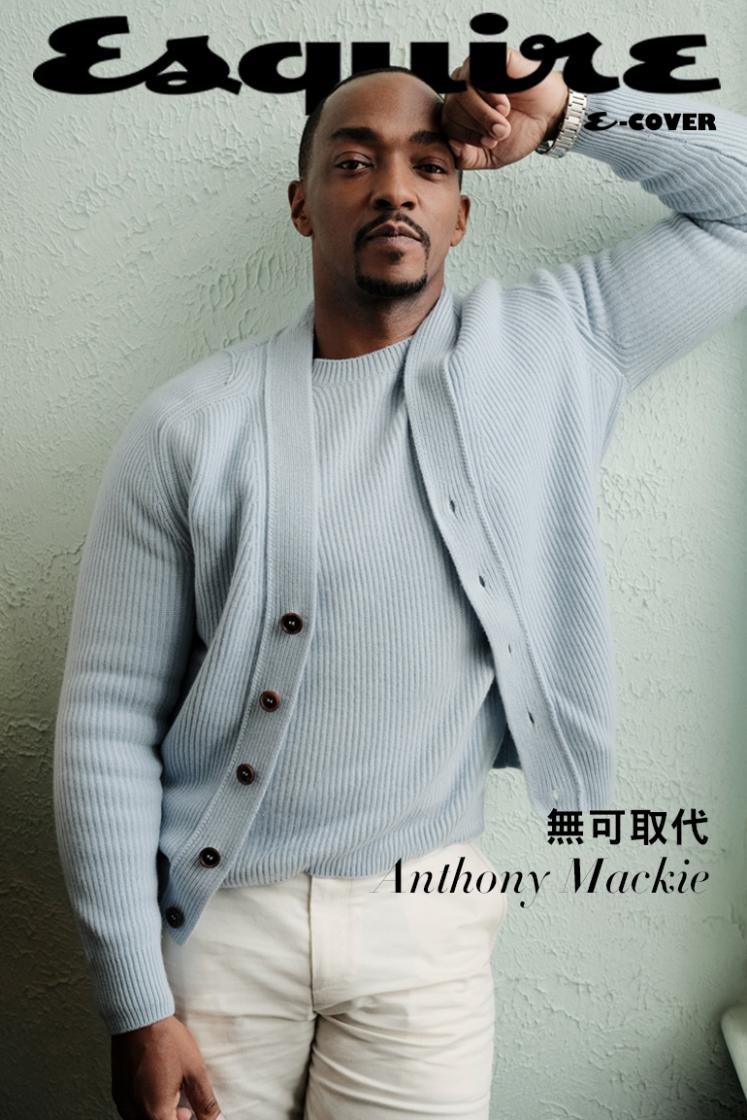坐在螢光幕前,你要選紅色藥丸或是藍色藥丸?無論選擇何者,在兩個小時半的光影轟炸後,我們都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虛擬旅程,在過程中幻想和真實沒有分界,那是人類想像力光芒閃亮的一刻,也是科幻電影賜與我們的美好娛樂。
「好奇心」為科幻之母
1977年由美國太空總署透過航海家太空探測器,向浩瀚太空發射了兩張金唱片,在太空中飄流的兩張碟片,裝載著人類存在的信息,更是智慧生物在宇宙中存在的證明。無法停止追尋的腳步,探索未知是人類的天性,除了太空旅行外,所有科幻的題材總不免圍繞著生命的起源、人類存在的意義。 雷利史考特風格多變,導演的題材多元,曾經打造的科幻經典影響了整代人,包含《異形》和《銀翼殺手》都是一例。 知名科幻電影大導雷利‧史考特爵士(Sir Ridley Scott,下簡稱雷利)2012年在接受美國版《Esquire》採訪時曾說道:「夜晚凝視著星空時,你我可能都會有些相同的想法,這是老生常談了。當看著夜空中的銀河時,難道不曾感到自己的渺小嗎?這和有沒有信仰無關,我只是不相信人類在宇宙中是孤獨的,在地球之外,必定有種我們還沒發現的生活方式。」雷利提出的觀念,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恰好是一切科幻電影的基礎,那就是:「好奇心。」也唯有保持好奇,人們才能不斷在科學上進步,創造更好的生活價值。
未來的樣貌 科幻電影知道
火星上的荒漠是《絕地救援》等電影對真實景況最好的模擬。科幻電影替我們在某件事情實現前先預演,是對未來種種可能發展的預測與排練。或許我們還沒有《星際大戰》裡的太空船大戰與光劍、《回到未來》穿越時空的未來車、《星際效應》中穿梭黑洞的太空船,更沒有《侏儸紀公園》裡基因改造的恐龍和《銀翼殺手》裡隨意行走,擁有豐富感情的人工智慧。然而依賴想像力所設計的情節,架構在某個程度的科學現實上,替我們在某種未來科技實現前預先排練,這種建構於真實之上的虛構,更顯得引人入勝。
 《異形》系列創造了太空旅行、密閉空間與駭人怪物等三元素合一的恐怖驚悚電影類型。
《異形》系列創造了太空旅行、密閉空間與駭人怪物等三元素合一的恐怖驚悚電影類型。
 《異形》距今將近40年,電腦也不再是大按鍵跟32位元的作業系統,但對於DNA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的想像卻非常前衛。
《異形》距今將近40年,電腦也不再是大按鍵跟32位元的作業系統,但對於DNA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的想像卻非常前衛。
所以看完《駭客任務》後,你會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錯選了紅色藥丸,才會來到「沙漠般乾枯的真實荒漠」(the desert of the real),想想自己昨晚喝的那杯燙手咖啡,是否也是母體造假的記憶之一。就像哲學家柏拉圖提出的洞穴寓言,古老聚落的囚犯在看完無數光影所演繹的虛構現實後,終於發現自己被綑綁在洞穴中,自由本來就是種幻覺,自身不過是幻想的囚徒。先不從這個哲學小故事中,討論世界是否只是針對理想世界的模擬,事實上我們所打造的科幻電影場景,每一個畫面都是未來世界的某種想像,會不會有一天忽然實現誰也說不準。
 1999年的《駭客任務》創造了幾個至今討論不斷的話題,當然包括慢動作的:「子彈時間」。
1999年的《駭客任務》創造了幾個至今討論不斷的話題,當然包括慢動作的:「子彈時間」。
多數的科幻電影總是有濃厚的悲觀氣氛,要嘛是在火星失去了一切救援機會,再不然就是帶著超高科技上太空,卻不免要被未知的破胸異形追殺,更不要說大多數的人工智慧都懷抱著消滅人類的心思。雖然電影終究不是現實,九零年代的科幻片也多少有些對科技失控的焦慮,不過從《科幻電影的預言與真實》書中,量子物理學家邁克及電視節目主持人瑞克的閒聊聽起來,現今的科學似乎還沒有暴走失序。目前為止,還不用擔心哪位瘋狂科學家不小心讓喪屍病毒外洩,更沒有外星飛船突然攻打地球,或是誰改變了時間軸,讓校園惡霸變億萬富豪。不過剛經過街上,斑馬線上那隻黑貓好像經過了兩次,我是不是看錯了什麼?
如果你不滿每天忙碌的生活、客戶無理的要求與老闆毫無道理的咆嘯,多希望一切都是母體所虛擬的假像,那讀讀量子物理學博士邁克及BBC電視節目主持人瑞克的力作應該很紓壓。探討分析九零年代諸多經典電影裡,種種虛構科技背後相關的知識。兩人透過一部電影一個章節的對話,開啟一連串對科學現實的討論,你要說是插科打諢的胡說八道嗎?說真的,這種高密度等級的閒聊,搭車時隨手抽一篇來讀,還頗有趣味。
Text by 黃博鉞 Images: courtesy of Getty Images、方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