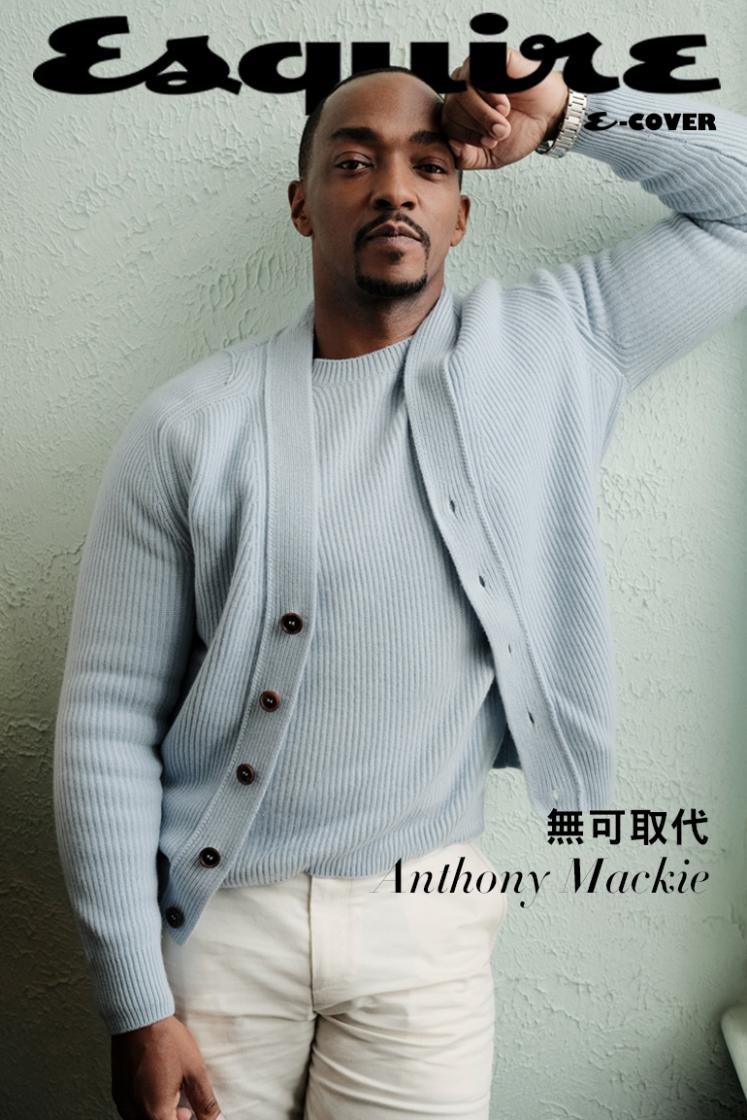十天前,我端坐在台北市繁華鬧區的一間靜謐藝廊之內,耐心等待IWC萬國錶讓我們搶先預覽今日於日內瓦「鐘錶與奇蹟」(Watches & Wonders)高級鐘錶展上所推出的最新腕錶作品。按照慣例,IWC萬國錶每年在日內瓦所發表的新作,都將圍繞單一個系列開展,不只主題明確,錶款陣容也十分精彩,每次才剛看完當年度的新作,便讓人忍不住開始猜測明年又將端出什麼菜。只不過,當天踏進藝廊之前我所抱持的那份好奇與期待,卻被藝廊白淨牆面上的一串德文給意外劇透,「原來是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啊!不意外啦,畢竟這幾年精鋼運動錶這麼紅,也該是時候輪到工程師出頭了。」
對比當時的冷靜自持,如今端坐在電腦之前的我心情卻十分激動。那股澎湃之情,一部分是因為今天終於在日內瓦見到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的廬山真面目,但絕大部分則來自於重新認識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的過程,所賦予我一連串的感官刺激;那感覺就像看完一部高潮起伏不斷、揉合命中注定及偶然巧合的小說,又或者是一個如何在危機四伏之下矢志不渝捲起千堆雪的故事,而主角除了一位天縱英才、一位嚴謹的工程師之外,還有一位奉行完美主義的繼承者。

危機四伏
故事是以不安拉開序幕。上世紀70年代美國本土的反戰聲浪達到高峰,激進份子先是開始以暴力脅迫政府在越南議題上退讓,但隨後越共的農民革命意志徹底戰勝了美國在軍事與資本的壓倒性優勢。在尼克森因水門案黯然下台之前,為了解決越戰龐大的軍事開支,他在1971年單方面宣告美元貶值及美元停兌黃金,不只讓布列敦森林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面臨崩潰,國際金本位制度也隨之告終,世界各主要貨幣被迫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不過兌換美元的匯率依舊直線下跌,金價更飆漲得一塌糊塗;光在1971年到1974年之間,每盎司的黃金價格更足足漲了三倍。此外,1973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更進一步加劇了西方各國的經濟衰退,面對局勢不穩及各種不確定因素,消費者在購買力下降之後更是信心全無,企業獲利被大幅壓縮,只好開始裁員及減少投資,造成更嚴重的停滯性通膨。
在二次大戰倖免於難的瑞士,卻沒能逃過這次的世界災難。引以自豪的製錶工業,原本就因瑞郎兌換美元匯率下跌造成鉅額損失,不過金價飆漲更給予致命打擊,因為當時絕大多數的腕錶均以黃金為首的貴金屬所打造,漲上天的金價不只造成原料短缺、成本陡升,且進一步推高腕錶的售價;不令人意外的,那也全反應在急遽下滑的腕錶的銷售與出口數字。在資本緊縮的情況之下,錶廠不僅發不出製錶師的薪水,低落的產能更可能嚴重衝擊製錶業命脈:錶廠無法順利累積與傳承經驗,更無力研發與時俱進的全新技術。
無獨有偶,70年代憑藉價格與產量優勢而風靡全球的石英錶,更讓當時危機四伏的瑞士製錶業更顯岌岌可危。過往機械錶所強調的耐用與精準,如今放在廉價卻精準無比的石英錶面前,變得蒼白無力且一文不值。而上述這個由金價飆漲、經濟蕭條及石英革命等一連串事件所引發的完美風暴,正是IWC萬國錶今日所推出的工程師系列自動腕錶之原型——1832型工程師SL腕錶的誕生背景。

極客工程師
相較於其他錶款,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其實更能忠實體現IWC萬國錶的製錶精神:以實事求是、嚴謹的態度同時展現「技術」與「設計」(這也是十天之前,我在台北藝廊牆上所看到的兩個關於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的關鍵字)。二戰之後的歐洲雖然百廢待舉,不過卻是一個從戰後匱乏之中屢獲創意、不分領域全力革新與發展的時期,讓當時的人們深深著迷於科技,且相信科技的發展將無遠弗屆。而工程,正是那個時代創新、進步與繁榮的象徵,不僅為各式建築與設計打下基礎,也大量用於各種前所未見的產品與裝置。那一股對於科技進步的樂觀態度與信念,即為IWC萬國錶推出工程師系列(Ingenieur;在法語及德語之中意指「工程師」)的命名由來。
回溯那個年代的錶壇,自動上鏈機芯正逐漸成為市場主流,如何提升上鏈效率,因而成為錶廠技術較勁的重點。時任IWC萬國錶的技術總監比勒頓(Albert Pellaton)於50年代推出首枚自製自動上鏈機芯,並配備創新的比勒頓上鏈系統(Pellaton winding system;俗稱啄木鳥上鏈系統),那是藉由猶如鳥嘴的棘爪,驅動連接發條盒棘輪的上鏈機制,只需最輕微的擺動,即可透過雙向轉動的擺陀為主發條快速上鏈,效率非常高,至今仍是不少鐘錶玩家與藏家津津樂道的話題。
作為IWC萬國錶旗下第一款民用防磁腕錶的工程師系列,也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誕生。第一只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腕錶(666型)於1955年推出,最初是針對工程師、物理學家及醫師等經常得在強烈磁場環境下工作的專業人士而打造。它所搭載的8531型機芯,正是比勒頓為IWC萬國錶研發的首枚自製機芯,不僅配備上述比勒頓上鏈系統,其軟鐵內殼能有效保護機芯免受磁場干擾,同時避免零部件磁化而影響腕錶走時精準;而該項創新技術,是IWC萬國錶早在幾年之前打造「飛行員系列馬克十一」腕錶時便已研發完成。
初代的IWC萬國錶工程師腕錶,與今日面貌其實不盡相同,它具備渾圓且低調的錶殼,同時也有服膺時代美學而以黃金打造的版本,IWC萬國錶隨後於1967年延續了此一設計,推出了第二代的866型IWC萬國錶工程師腕錶。然而,根據60年代末錶廠高層的會議紀錄,他們當時正計畫推出一款「嶄新、扎實且以精鋼打造的IWC萬國錶工程師腕錶」,並希望導入防震系統,讓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成為名符其實、堅固耐用的腕錶作品。遺憾的是,分別於1970及1971年誕生的改款原型,不僅均未通過衝擊測試,接踵而來的暴漲金價、暴跌的美元匯率,以及暴衝入市的石英腕錶,都讓IWC萬國錶及至整個瑞士製錶業皆無暇他顧且疲於應付。
據IWC萬國錶當年的行銷與銷售主管Hannes Pantli回憶,70年代彷彿一場沒有盡頭的生存戰,他們得使出渾身解術才能讓IWC萬國錶活下去,確保多年來所累積的技術與經驗能繼續留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IWC於瑞士東部的總部所在地城市)。在缺乏資金,同時還得持續營運一間擁有150位員工的錶廠的艱困情勢之下,IWC萬國錶除了也開始製作石英錶之外,同時還找上一位來自日內瓦的天才製錶師,試圖為性格宛如IWC萬國錶一般的工程師系列扭轉乾坤,重獲新生。

天才設計師
IWC萬國錶當時從外部找上的腕錶設計師,正是在70年代成功開創前所未有的奢華精鋼腕錶的Gerald Genta,除了IWC萬國錶的工程師系列之外,包括愛彼的皇家橡樹系列及百達翡麗的金鷹系列,都出自這位天才之手。不過,少有人知道的是,早在皇家橡樹系列於1972年推出之前,IWC萬國錶在那五年前其實就曾找過當初為自由接案身份的Gerald Genta設計一款精鋼計時腕錶,只可惜該案後來沒有付諸實現。憑藉Gerald Genta的巧手與創意,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不僅有了截然不同於初代的樣貌,同時奠定了該系列辨識度十足的DNA,就連此後數十年間該系列數度設計微調,也都有了絕佳的參考模範,同時依舊保有這位天才獨有的藝術風格。
「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之中,我曾未見過他做出任何有違信念的事,更不曾為了銷售而更改設計;若真在製作過程改變設計,也是出於技術問題。」與Gerald Genta結褵多年的Evelyne Genta曾在訪談中如此說道。她笑稱,這位世人眼中的天才與大師,確實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且不可思議的事,好比他每天早上起床好像就知道當天想要設計些什麼,而且他設計的速度飛快,彷彿在下筆前腦中已有腕錶最終的樣貌了,「Gerald不太講究工作的地點與方式,不僅從未追求非得在安靜的地方獨處,也隨時隨地都能進行設計,彷彿對他來說一切都是設計。不過,他常跟我說,自己的靈感都是從天而降,而且他繪製的設計圖也總是十分貼近腕錶的最終成品,這點真的很神奇。」
正式委託Gerald Genta重新設計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之前,IWC萬國錶不僅已順利打造出精良的8541型自動機芯(改良自比勒頓所研發的首枚自製8531型機芯),且亟欲擺脫對金質腕錶的過度依賴。最終,這位橫空出世的曠世英才,在1974年提交了全新的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設計草圖,而那一枚至今仍讓許多錶迷津津樂道的腕錶具備了幾項特色,包括共有五個鑽孔的懸入式錶圈、棋盤圖樣的錶盤,以及搭配H鏈結的一體成形式鏈帶。經過兩年的研發,名為「1832型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SL」的腕錶,最終在1976年的巴塞爾鐘錶展上亮相,不論就超大號尺寸(40毫米)或令人咋舌的高昂定價(2,000瑞士法郎)來看,它注定都是一只留名青史的腕錶。
工程師腕錶之外,在Gerald Genta在1972至1976年間,陸續創作出數款精鋼運動腕錶,成功引領了至今影響力不墜的精鋼運動錶風潮,雖然此前確實沒有任何錶廠考慮推出精鋼材質的腕錶,遑論定價如此高昂,不過彼時精鋼運動錶的誕生,其實也與國際金本位制度崩潰、金價暴漲脫不了關係。從設計角度與時代意義來看,IWC萬國錶的工程師SL腕錶雖是不可多得的作品,不過可惜的是,它從未取得商業上的成功。8541型機芯不僅讓這枚腕錶過分厚重(以至於後來它還被冠上「Jumbo」(超大號)的暱稱),上手後更在腕間顯得大而無當。
由於彼時正值石英錶大舉入市,客戶多半偏好扁平、輕薄且售價低廉的石英錶,因此在工程師SL腕錶推出後的六、七年之中,僅售出1,000多枚腕錶而已,而且還是加上後續結合精鋼與黃金的雙色金,以及搭載石英機芯的版本的銷售數字。不過,這仍舊無法抹滅Gerald Genta耀眼的成就,表面上他打造了一種全新腕錶類型,實則為當代錶壇開創出一種前所未見、獨樹一幟且歷久彌新的風格美學。

完美繼承者
今天,IWC萬國錶在日內瓦的「鐘錶與奇蹟」高級鐘錶展上,發表三款全新打造的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自動腕錶40。三件新作承襲Gerald Genta於70年代重新設計IWC萬國錶工程師系列所推出的1832型工程師SL腕錶,在忠於原作的前提之下,包括風格、細節、技術及人體工學等,皆迎來更富現代感的嶄新詮釋。而對IWC的設計總監Christian Knoop來說,從1976年走到2023年的這一段旅程絕非輕鬆,研發過程早從幾年前便已著手進行,不只微調了錶殼比例,包括飾有五個多邊螺絲鑽孔的錶圈、錶盤的浮雕結構、錶鏈採用隱藏插針的閉合鏈結設計,以及為了找到最服貼舒適的佩戴體驗,進而更動錶耳設計並改良錶環曲線,不僅更符合人體工學,且絲毫無損原有的設計美學。
十天之前,當我在台北藝廊搶先佩戴新款的IWC萬國錶工程師自動腕錶40時,確實對它符合人體工學的佩戴體驗非常有感。1976年推出的IWC萬國錶工程師SL腕錶不僅鏈帶較寬,且配備鼻型錶耳,進而拉長了錶殼線條;若佩戴者的腕圍較窄,便會影響佩戴時的服貼度與舒適感。由於本身即屬於手腕較細的人,所以過去我在挑選手錶時,會特別留意上下錶耳的距離;當距離愈寬,則愈有卡手的感覺。別看一只腕錶或許錶徑寬闊,若它的上下錶耳距離不過長,其實手腕細的人也能輕鬆駕馭。新款的IWC萬國錶工程師自動腕錶錶徑雖達40毫米,不過或許是因為微調了錶殼比例,錶耳也改為帶有H鏈結的一體成形鏈帶,才讓這款精鋼鏈帶運動錶戴起來特別舒適服貼,錶徑在視覺上不僅要比實際來得小,整體看來更有一股geek chic的簡潔俐落感。
「重新詮釋IWC萬國錶工程師SL腕錶這樣的經典創作,這機會可不是每天都有,所以我們以謹慎的態度檢視每一個環節,即使微小細節也追求完美,我認為我們不只成功創造出全新的現代演繹版本,新款IWC萬國錶工程師自動腕錶40也完美展現了IWC萬國錶的卓越工程技藝」,自稱為「完美主義者」的Christian Knoop如此說道。訪談間,他提到過去IWC萬國錶工程師SL腕錶錶圈上的五個鑽孔是以旋扭方式固定於錶環之上,因此鑽孔位置是隨機的,且從來不會出現在同一個位置上。
那種「隨機感」深深困擾著身為完美主義者的Christian Knoop,所以他不僅為新款工程師自動上鏈腕錶40換上真正的多邊螺絲,且讓錶圈上的五顆螺絲在發揮實際功能(固定錶環)的同時,也能維持在同個位置上。這樣略帶古怪的堅持與不妥協,不僅令人莞爾,也能清楚見識到作為設計總監的Christian Knoop,努力取得技術與設計完美平衡的決心。但也正是這份心意,讓我看到同為IWC萬國錶工程師與設計師的Gerald Genta與Christian Knoop同樣不曾留戀過往,而是持續追求進步與完美的精神,此與IWC萬國錶的工程師性格不僅如出一徹,且完美繼承了所有令人動容的品格。
回想十天前,我不曾想過一只腕錶能夠看見這麼多高潮迭起,而不論是天才、工程師抑或繼承者的故事,都將與我手腕上新款的IWC萬國錶工程師自動腕錶40緊緊地連在一起。

Text by Adrian Chou Images:courtesy of IWC萬國錶
延伸閱讀:
誰的低調能比我更高調?戴上這枚腕錶,別人看不到你張揚酷勁的車尾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