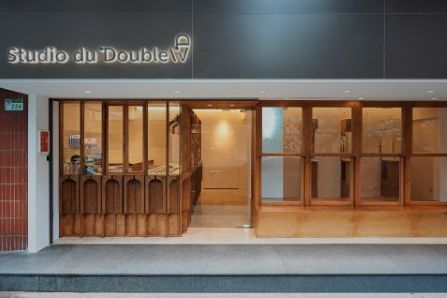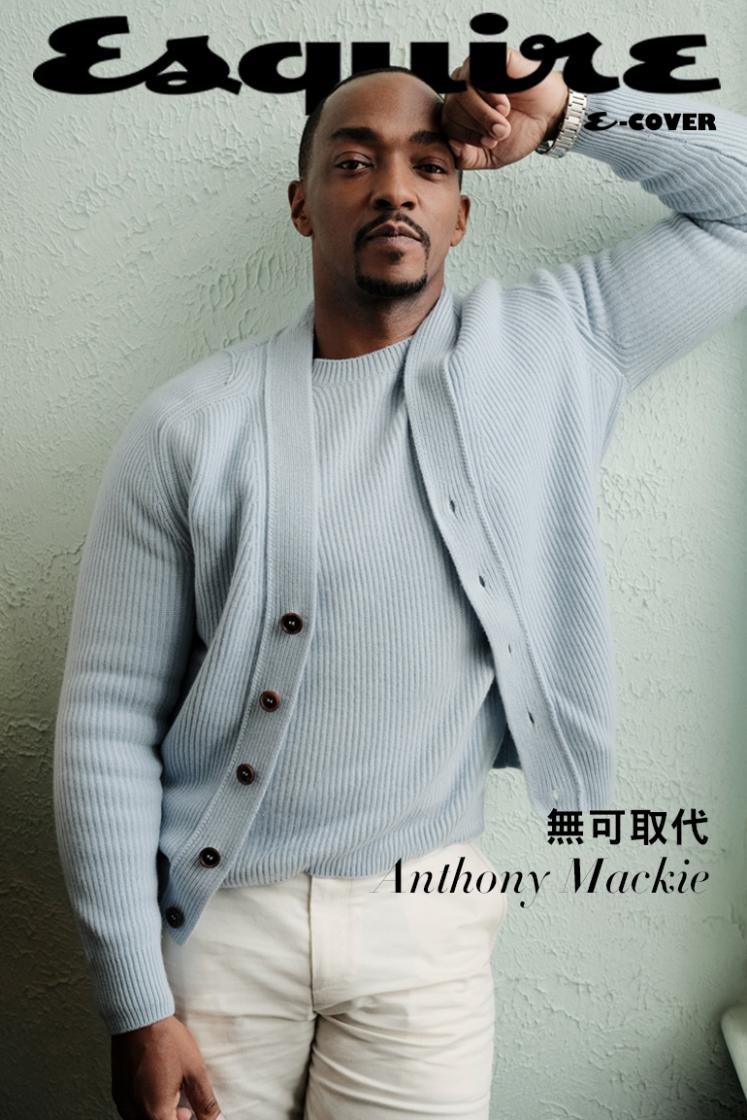「喝酒吧!因為從來沒有一個精彩故事,是從吃沙拉開始的。」臉書上的迷因圖總是這麼寫。但我想反問一句:你喝過用番茄做成的雞尾酒「Tomatini」嗎?這杯酒略帶泡沫,色澤正如你想像中那樣,看起來就像一碗現做沙拉。入口時,首先是巴薩米克醋的微酸餘韻,接著伏特加的勁道悄然湧現。當我走進La Petite Maison位於倫敦的高級分店時,眼前的景象讓人會心一笑:燭光搖曳下,每張餐桌上幾乎都擺著一杯剛調好的Tomatini。這杯酒的誕生地正是這裡,而我也很識相地,在主菜送上來之前,默默續了第二杯。
「我覺得調酒師應該都挺討厭我的,因為調一杯Tomatini實在太費工夫了。」Jimmy Barrat第二天早上跟我說道。我喝完酒有點宿醉,還真得怪他。2010年,他在籌備La Petite Maison杜拜分店開幕時,發明了這款Tomatini。他想調出一款能「喚起思鄉之情」的調酒,對這位來自尼斯的調酒師來說,家鄉的味道就是牛番茄。將這種嚴格來說屬於水果的蔬菜打成泥,加入伏特加和醋,再撒上現磨黑胡椒,一杯全新的經典就此誕生。除了「好喝到爆」這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款飲品會大受歡迎其實不難理解:任何人都能復刻,而且在這個以冰鎮經典調酒為主流的行業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Barrat表示,「我不太愛說『跳脫框架』這種話,但我認為我們可以把那個框架變得更大。」
鹹味雞尾酒其實並不稀奇。數十年來,我們早已習慣深夜小酌一杯髒馬丁尼、隔日早晨靠血腥瑪莉續命的生活節奏,如今鹹味雞尾酒風潮正再次席捲而來。當倫敦的必訪餐廳Julie's於2024年重新開幕時,菜單上便推出一款以辣根芹菜醋液與龍蒿油調製的綠番茄馬丁尼。而我個人鍾愛的Three Sheets酒吧,有一款以甜菜根為主角,讓人喝起來像是在樹籬間大口痛飲烈酒的大地馬丁尼。而如果有天你宿醉醒來,走進莫里波恩區的義式餐廳Lavo,點上一杯血腥瑪莉,端上桌的會是升級版:帶著義大利羊奶起司香氣、風味濃郁的鹹香之作。如今只要翻開倫敦任何一家酒吧的酒單,幾乎都能看到鹹味系的各種變奏:有的以鯷魚油取代橄欖鹽水,有的加入蘑菇泡沫,或是搭配大量發酵蔬果。
位於梅費爾區的地下酒吧Nipperkin,靈感源自日式的音樂欣賞空間。我在那裡品嚐到一杯令人印象深刻的調酒,以韭蔥浸製蒸餾酒為基底,融合松露琴酒與醃洋蔥苦艾酒調製而成。那裡的酒單隨著時令變化,根據當季食材重新構思調酒的風味組合。那杯酒味道濃郁厚重,初入口時確實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顯然不只我有這樣的感受,主理人Angelos Bafas告訴我,菜單剛推出時,不少客人要求更換,還誤以為拿到的是餐點菜單而非酒單。然而,這些以鮮味為主調的創意調酒,搭配店內實際供應的日式下酒菜,卻意外地相得益彰。也許,一個精彩的故事真的可以從一杯「沙拉系雞尾酒」開始,或者說,從「當季」這個概念開始。

在這段既痛苦又愉快的調查初期,我原本有個小小的理論:鹹味調酒之所以受歡迎,也許是因為不像甜酒那樣容易讓人隔天頭痛。但Barrat笑著說,其實酒界早在多年前就靠更健康的糖解決這個問題了。鹹味系酒款其實還有個顯而易見的優點:減少浪費。我訪問過的調酒師們無不對此讚不絕口,像是把剩下的紅蔥頭直接丟進果汁機,或是以當季當地的蔬菜取代過季食材……當然,能創造出這些作品的調酒師,多半也都帶點瘋狂。
說到這一定得提一下瑞典名廚Niklas Ekstedt在倫敦開設的餐廳Ekstedt at the Yard。那裡的招牌之一,是一杯用油洗工法打造的古典雞尾酒。放在我眼前的這杯酒,色澤澄黃,幾乎像是天使親手釀製的作品,但其實製作過程比外表複雜得多。我被領進廚房,親眼看見廚師以牛油炙燒牡蠣。我一邊吃著熱騰騰、鹹香濃郁的牡蠣,一邊看著他熟練地收集烤盤上的牛脂。這些牛脂會與干邑白蘭地混合,靜置浸泡數日,之後撈除凝固脂肪,只留下融合香氣的酒液,成就這款古典雞尾酒的全新變奏。喝起來像古典雞尾酒,也像牡蠣,又帶著一點牛排的風味。這大概是我喝過最具挑戰性的酒,第一口甚至讓我覺得應該搭配刀叉上桌。但只要細細品嚐個三口,就會瞬間被征服。
雞尾酒是用搖的還是攪的?誰在乎!只要是鹹的,就沒錯!
Text by Henry Wong|Translation by Min Kao|Edit by Gary Liu|Images: courtesy of 達志/Shutterstock
延伸閱讀:
化平凡為非凡:Krug香檳聯手米其林三星JL Studio、二星Meta四手聯彈共譜風味交響